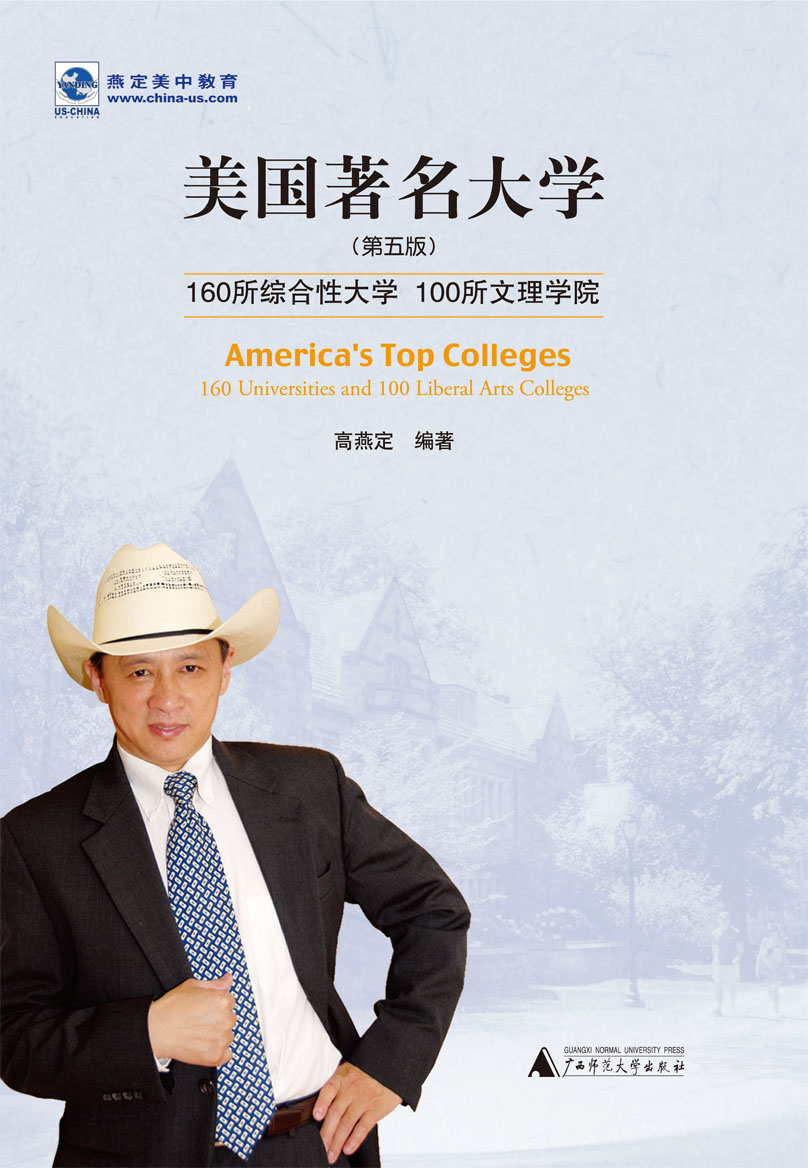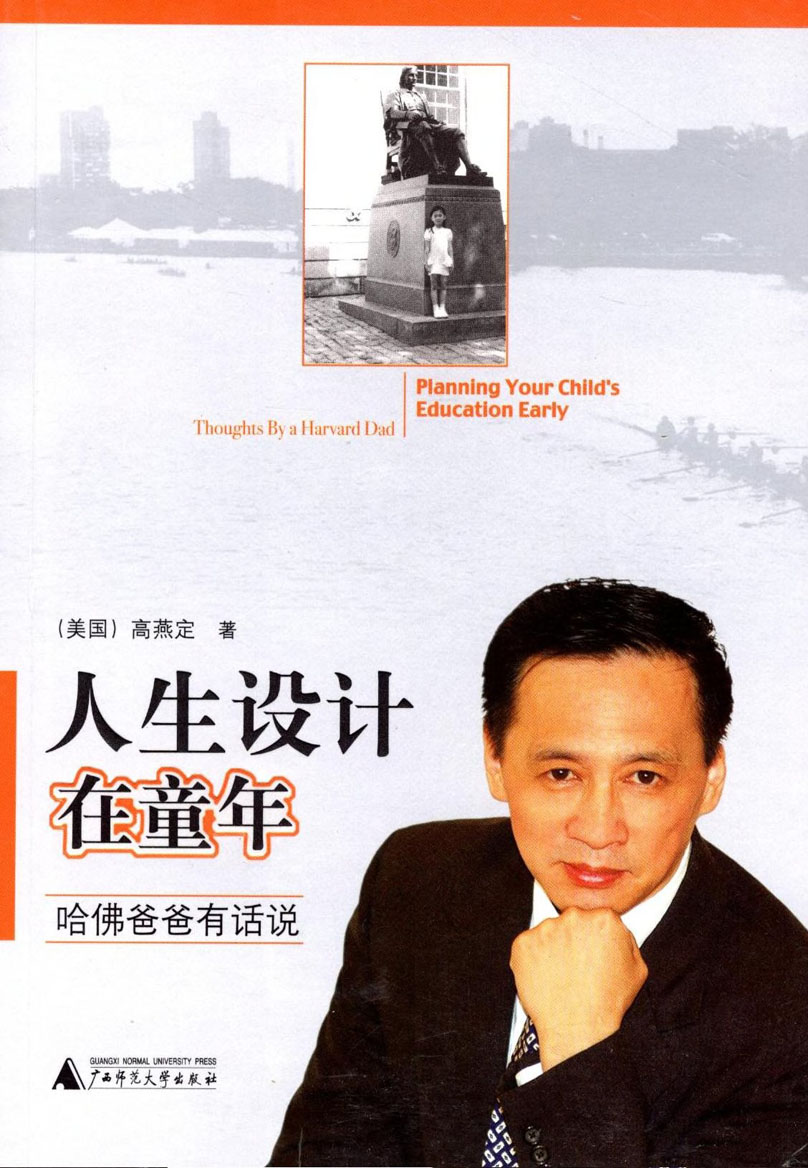两代人的留学梦 | 哥伦比亚大学华裔博士喻俐雅毕业演讲:将困惑变为成长的动力!
来源:www.china-us.com 作者:燕定美中教育 发布日期:2017年05月16日 03:05
摘要:
昨天,在2017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典礼上,在中国出生,德国长大的政治系博士喻俐雅代表全校数百位博士发表了毕业演讲。值得注意的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由一名华裔博士生在博士毕业典礼上致辞,这如果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至少也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
昨天,在2017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典礼上,在中国出生,德国长大的政治系博士喻俐雅代表全校数百位博士发表了毕业演讲。
值得注意的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由一名华裔博士生在博士毕业典礼上致辞,这如果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至少也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
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喻俐雅来到了哥大攻读政治哲学博士学位,这期间,她还在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过一门交叉探索性学科。喻俐雅的博士论文是一项跨学科的工作,论文中,她运用社会神经科学中关于偏见、刻板印象、以及对他者非人化态度的研究,针对我们如何能够在高度多元与割裂的社会中合作共处的问题,发展出了一套相应的神经政治学理论。
如今,在这次的演讲中,她回答了这个时代留学生子女都会碰到的身份困惑问题。她从身边的日常纠结开始,探索人性和历史的本质,并将困惑变成成长的动力!
其实,喻俐雅的成功不仅得益于自己为学术梦想坚持不懈的努力,也离不开其家庭的影响。
喻俐雅的父亲喻恒是早期的留学德国的留学生,像许多老一辈留学生一样,喻恒先生在事业上不断创造辉煌,20年前引进的德国水性环保涂料都芳漆,如今在中国已成为最大的环保涂料品牌。他也被媒体誉为中国环保漆之父。在事业成功后,他还积极投身于各种公益活动,例如:2002年,喻恒通过报道知道了传统内蒙古家庭的锅连炕缺陷后,大为震惊,当时就飞赴呼和浩特的解放军253医院,为几十名烧烫伤儿童的的康复资助手术费用,他通过长期奔走和呼吁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责成自治区政府下文采取措施,帮助有五岁以下儿童的农村家庭进行了锅、炕有效隔离改造。终止了每年当地锅连炕烧烫伤3000儿童,死亡800儿童的悲剧。
前不久,他还建立了喻艺术基金会,专门帮助中国青少年提琴家使用名琴参加国际比赛。作为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理事,在2005委员会年会上,喻恒与杨澜一起获得了“中国名片奖”。
以下为喻俐雅中英文演讲稿👇👇👇
喻俐雅 / 政治学系:
亲爱的寇兹沃思校务长,麦迪冈常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阿隆索院长,各位老师与行政员工;亲爱的家人朋友,以及最重要的,亲爱的2017届博士毕业生们:
今天能够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我感到极其荣幸。我首先要感谢我在政治学系的两位导师,戴维·庄士敦和杰克·斯奈德;我的几位答辩委员:罗伯特·杰维斯,来自教师学院的海伦·维尔德利,和拉萨纳·哈里斯;以及今天在台下就座的,我的父母、丈夫、儿子和朋友们。
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个“地方”,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在我抵达时弥漫着无限可能性的神秘的地方,一个标记着我的智识成长的地方,一个为我的多重身份提供了相互对话空间的、有迹可寻的地方。
七年前初次体验这个校园令人迷醉的夏夜时,我和一位刚刚结识的朋友坐在洛氏图书馆的台阶上,看着对面巴特勒图书馆的灯光一个窗子接着一个窗子亮起,渐次穿透正在变暗的柔和天幕。我和这位朋友讨论到,对于我们这样高度流动的一代人,生活的地方和居所如何常常毫无确凿次序可循地叠垒在一起,而对具体年份的讲述则有助于其结构化和清晰化。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关于我们去过或来自的所有那些地方的记忆、关于我们抛在身后或亟待融入的所有那些地方的记忆,都会迅速缠绕成一团由事实堆砌而成的、令人头昏脑胀的乱麻。相反,具体年份则逐渐成为我们梳理自身经历的出发点——仿佛巴特勒图书馆的那一排排窗子,在我们眼前亮起,照向黑暗的夜空。
不过今天我特别想说的是,关于哥大的记忆,对我们这样高度流动的一代人而言尤为珍贵,因为这样一个地方所留下的记忆与体验,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深入骨髓的烙印。
进入哥大之前,我在英国学习政治哲学、在德国长大、在中国出生。因此伴随我抵达哥大的,是我对自身文化归属与智识归属的无数问号。
我的博士论文是一项跨学科的工作,运用社会神经科学中关于偏见、刻板印象、以及对他者非人化态度的研究,针对我们如何能够在高度多元与割裂的社会中合作共处的问题,发展出一套相应的神经政治学理论。哥大的校园,那些筑于战前的楼里刮着穿堂风的长廊,那一个个研讨室,一座座图书馆,以及最重要的,校园里的人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有迹可寻却又自成一隅的地方,令我得以身处其间,为自己相互冲突的各种身份搭建联系。
在学术上,哥大对我意味着这样一个地方:在我力图为当今的身份政治创建一套全新的神经政治话语和跨学科理论时,我可以说到做到,在几个小时之内“跨越”学科边界,用一整天时间走遍晨曦高地校区不同院系的办公室、研讨室、图书馆阅览室。就读研究生这些年里,每当需要思考脑神经如何影响政治、政治如何反映在脑神经中之时,我便在校园里信步漫游,通过穿越校园空间,将神经科学与政治哲学这两个迥然有别的智识领域在自己脑海里串联起来。
但是与任何能够攫住我们想象的现实空间一样,哥大这样一个地方,既激发着我们最天马行空的想法,同时也吸引着我们内心最脆弱的渴望。如果你和我一样,曾经在面对各种与生俱来却又常常相互冲突的文化、种族、语言和性别身份时,为你究竟是谁、究竟应当如何思考、究竟应当如何谈论自身,而困惑过、绝望过,那么你一定理解,像“归属”、“家园”、“解放”这样的词汇,绝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令人心神悸动的天籁,驱使你以一种近乎非理性的饥渴与决绝,去一探它们的究竟。
当我来到哥大时,我一心想要研究诸如种族、文化、阶级这样的社会身份,在我们所处的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影响力。由华裔父母在冷战以后统一的德国养育成人,构成了我兴趣的发端:我困惑于身份政治何以能够导致犹太大屠杀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同时又何以能够成就美国民权运动、反种族隔离、女权运动、殖民地解放这样激动人心的胜利。为什么二十世纪的身份政治造就了如许灾难与如许成绩?我们能从中为二十一世纪的身份政治、为我们这个日益高度多元与割裂的社会,汲取怎样的经验教训?
不过当然,正如现实中常常发生的那样,这些问题背后最深的、最隐蔽的、同时也最刻骨铭心和最强大的驱动力,其实源于我对自身“自我”的困惑。源于我自己作为一个跨文化的少数族裔女性,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无所归依的体验。源于我在华人同胞眼里太过“西化”,在西方同僚、教授、朋友眼里又太过“外族”,而屡遭排斥的体验。
源于我不知道哪家历史真正写就了我、我又应该帮助书写哪家历史的体验。源于我对一个可以称为我的智识家园的地方的向往:这样一个地方,能够给予我归属感,而不把我划入一系列身份范畴;能够允许我提出问题,并以一种干脆利落、不大惊小怪、令我得以全神贯注于问题本身的方式全力寻找答案。
在这样一个地方,许许多多像我一样从身份认同的边缘地带迁至中心的人们,每天醒来时能够不必再被刺骨的羞愧感萦绕。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你曾经是怎样的人不再重要;在那里,你每时每刻在研讨室、实验室、教室里的言谈、思考、回应,都能获得认真切实的对待。哥大这个校园,纽约这个城市,恰恰是这样一个令“归属”、“家园”、“解放”之类词汇焕发生机的地方。
话说回来,我也并不想过分美化哥大:我对哥大的记忆同样包括了围绕对这个地方的解释权——谁能得到代表、谁被允许进入——的斗争。我还记得身为学生会代表参与的历次激烈讨论,比如因为预备军官训练团重新入驻校园而引起的就哥大全球身份的讨论,和关于哥大在投资方面的伦理责任的讨论,也记得低收入学生敞开心扉讲述他们面对食物券与财务困难的挣扎,记得“黑人性命举足轻重”的示威,记得2016年学校史无前例地树立了一块勒纳佩部落纪念碑。
所以回想起来,我在哥大的时光,既充斥着这个地方为和我一样的跨文化人群提供的解放,也时刻伴随着一种警醒:这个地方需要由各种不同的声音来不停地抗辩、争取、和转化。
一个地方的意义,同样来自别人眼中的审视。如果不是因为我教过的本科生,我不会成为今天这个人——从校园里最年轻世代的视角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身份挑战,令我深深地反躬自省,也为我提供了真正的快乐与目的。同样地,与我们分享今天这一特殊时刻的父母家人们,也各自有着他们自己关于其它大陆、其它历史、其它政治时代的知识——正因如此,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个城市、这个时刻看到我们登台,对我们固然有着深深的触动和意义,但对他们恐怕更是如此。
亲爱的2017届毕业生们,请随我一同回想巴特勒图书馆渐次亮起的灯光,一如想象即将在我们毕业后渐次展开的年华,也请与我一同回味与哥大这个地方紧密相连的——终于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为你内心深处支离破碎的身份认同找到启蒙与意义、终于在某时某地的某个港湾找到真正的归属——那种发自肺腑的感受。
Dear Provost Coatsworth,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Madigan, Dean Alonso, faculty,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dear families and friends, but most important, dear Ph.D. class of 2017, I feel extremely honored to deliver the student speech today, and would like to start by thanking my two advisers in th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David Johnston and Jack Snyder, as well as Lasana Harris from UCL, and my other committee members Robert Jervisand Helen Verdeli from TC; as well as my parents, husband, son and friends whoare sitting in the audience today.
I am here today to talk about what Columbia means to me as a place – as an enigmatic place of arrival and possibility, as a place that marks my intellectual biography, as a tangible place in which a multitude of my identities found a space to speak to eachother.
On one of my first lush summer evenings on campus seven years ago, when I was sitting with a newly made friend on the steps of Low Library, we were watching how the lights of Butler Library opposite of us were beginning to pierce brightly into the soft, darkening sky, one small window after the other. My friend and I talked about how for our hyper mobile generation, places and locations are often piled on to each other without clear order, whereas recounting specific years provides more structure and clarity. For this generation, the memories of places that wetravel to and from, and that we leave behind and immerse ourselves in anew, can quickly become a jumbled and be wildering collection of facts. Instead, specific years begin to structure us – almost as if they light up in front of our eyes, like the row of bright windows of Butler Library, into the darkness of the sky.
Yet today I want to make the case that our memory of Columbia is especially precious for a hyper mobile generation like ours, because it is deeply etched into us as a memory and experience of place, above all.
I came to Columbia from having studied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UK, I grew up in Germany, was born in China, and thus arrived at Columbia with many question marks about my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belonging.
I wrote aninterdisciplinary dissertation that employs the social neuroscience onprejudice, stereotyping and dehumanization of others, to build a neuropoliticaltheory of how we can live together cooperatively in hyper diverse and divided societies. Columbia’s campus, its winded corridors in the prewar buildings, these minar rooms, the libraries, and above all, its people became a physically tangible and contained place where I could draw connections between my conflicting identities.
Academically, it became a place where in my quest to create a new neuropolitical language and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for today’s identity politics, I could literally cros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by walking over to the offices and seminar rooms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library rooms on Morning side campus, within a matter of hours, within a whole long day. As I was contemplating during my graduateyears what impact the brain has on politics, and how politics reflects in thebrain, I criss-crossed campus and connected the disparate intellectual fieldsin my mind – neuroscienc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 by walking across the campusspace.
But just like any physical place that is able to grip our imagination, Columbia is a place that at once attracts our most daring visions and yet most vulnerable longings. If, like me, you have ever wondered and despaired about who you are, how you are supposed to think, and how you are supposed to talk about yourself in light of the often conflicting cultural, racial, linguistic and gender identities that you carrywithin you, then you will know that words such as belonging, home and liberation are not just abstract concepts but powerful and enticing sounds that compel youto explore them with an almost irrational yearning and resolution.
When I arrived at Columbia, I wanted to understand the force of social identities such as race,culture and class, in determining political outcomes in our post-Cold War worldorder. I was motivated by my upbringing by Chinese parents in post-War, unifiedGermany: I was puzzled how identity politics could lead to such disastrous out comes such as the Holocaust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at the sametime, how it could also lead to empowering triumphs such as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s and Desegregation in the U.S., as well as the Feminist Movement andpostcolonial liberation. Why did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lead tosuch disastrous and yet triumphant outcomes? And how are we to learn from this for the identity politics of the 21st century, in our increasingly hyper diverse and divided societies?
But of course, as is sooften the case, the deepest and most hidden, but also most desperate and powerful drive behind these questions came from my own Self. They came from my own experience as an intercultural minority woman, who did not know whether she belonged to the West or the East. From my experience of being rejected as too Western by fellow Chinese and as too foreign by fellow Western colleagues, professors and friends.
From my experience of not knowing which history was truly writing me, and which history I should help writing. From yearning for a place that I could call my intellectual home,where I belonged without being put into set identity categories, where I couldask questions and try to answer them in a crispness and unfussiness thatallowed me to focus completely on the question itself.
A place where the beginning of each day was not marked by that stinging sense of shame that still too many of us who move from identity margins into the center allow to washover ourselves. I was looking for a place where it didn’t matter so much whoyou once were but where what you said, thought and responded to in this very moment in a seminar room, a research lab and a lecture hall, took on importance and reality. Columbia as a campus and New York as a city became that place where the words belonging, home and liberation could be uttered completely anew.
However, I am not tryingto idolize Columbia: my memory of Columbia is also marked by contestation ofits place, and by who is represented and allowed entry here. I am thinking backof my time as student senator when I engaged in heated debates about Columbia’sglobal identity in light of ROTC’s return to campus, about Columbia’s responsibility to invest ethically, low-income students who confessed abouttheir struggles with food stamps and finances, Black Lives Matter demonstrations, as well as the historic erection of a plaque that honors theLenape people in 2016.
Therefore when I think back, my time here at Columbia is marked both by the liberation that the spaceoffers to intercultural people like me, but also by the constant awareness that this space needs to be continuously contested, reclaimed and transformed by adiverse assembly of voices.
The meaning of a place also comes from seeing it through someone else’s eyes. I would not be the person I am today without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at I have taught – to consider the identity challenges of our time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youngest generation on campus has been deeply humbling for me, giving me truejoy and purpose. Likewise, our parents and family who are sharing this special moment with us today carry within them the knowledge of other continents, histories and political eras – which is why seeing us on stage today, in thisplace, in this city, at this moment, is deeply touching and meaningful to us, but perhaps even more so to them.
Dear class of 2017, I leave you with this image of Butler Library’s lights lighting up like the years that are to unfold before us after our graduation, but also, with a visceral sense of place connected to Columbia – of that period in your life where the fractured identity parts within you found enlightenment and meaning, and a truesense of belonging in a single haven of time and place.
深入阅读 | 喻恒
留学为我带来一生中不尽的美妙邂逅
当我打开邮箱,正在阅读小平的约稿邮件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电的正是享誉国际的小提琴大师齐默尔曼。他激动的声音从遥远的德国传来,却仿佛近在我的身畔,我们交谈起来,不知不觉半个小时便过去了。
说起我跟齐默尔曼的相遇,始于今年的10月19号,那时他正在上海开音乐会,我带着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杜庞将军”,在后台与他见面。当时他只是试拉了我的小提琴三分钟,就立刻提出请求,要换上我这把“庞杜将军”去登台演出。
要解释个中缘由,还得再往前倒推8个月。当时由于赞助者西德银行破产,齐默尔曼不得不与他那把曾14年形影不离的、同样出自斯特拉迪瓦里之手的小提琴“音姬夫人”忍痛告别,在遇到我之前的这8个月里,他虽然也接受了许多名琴的赞助,可是却没有一把真正称心如意,这对一个演奏家来讲,是一种特别大的隐痛,他跟我提到过,他甚至一度有过放弃演奏事业的极端念头……
直到他又看到了我带来的“杜庞将军”,才恍然大悟:原来之前8个月的痛苦、犹疑、等待、焦虑,一切都是值得的,都是为了遇到这把真正的“神琴”所要付出的代价!他对我说:我们的邂逅,也许是上帝早就做好的最美妙的安排。
作为一名曾经的小提琴琴童,现在的企业管理者,我太能够理解齐默尔曼那种找到“梦想之琴”的欣喜若狂。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都是从一些最单纯的梦想开始,然后在这条逐梦的路上,才会不断地收获到一连串的奇遇吗?冥冥之中,是什么神秘的力量把我、“杜庞将军”和齐默尔曼连在一起?这就不得不说,是我把德国都芳漆引入了中国的创业,才让我有机会拥有这一把琴,而这又是另一段携手二十年的缘分。沿着这条线再往前追溯,则不能不提到我的留学生涯,如果没有留学德国的那段经历打开了我的视野,磨练了我对商业的敏锐嗅觉,则不会有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打开邮件,看到小平在信中说,要我们每个人讲讲“留学如何改变了我的世界,讲述那些最难忘的留学故事以及留学中所带来的人生改变……”,看着这段话,我仿佛瞬间坐进了行驶在时光隧道中的高速列车,在窗外的呼啸声中,不断撞开了一扇扇通往旧时回忆的大门……
留学带给我最初的环保意识和商业磨炼
1987年2月,在最天寒地冻的时节,我提着行李,并且特别带上了从儿时起就陪着我成长的伙伴——小提琴,踏上了西去欧洲的国际列车,最终目的地是慕尼黑。我要先在前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北站转车,这一段路程就要花掉七天八晚的时间。
一到火车上,我就施展自己的商业技艺,做成了第一笔跨国贸易。这是用两瓶二锅头在前苏联的餐车上换来了一周的餐票。之后几天的吃喝不愁了,我的心情也就放松起来,望着车窗外看不到尽头的冰天雪地,怀揣着无限美好的梦想,一路向西。
在北俄罗斯车站转车的时候,我在厕所里又做了跨出国门后的第一笔“大生意”,把我觉得样子有点老土的呢子大衣以50卢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当地人。抵达西柏林后,已经是半夜,没有开往慕尼黑的班车,我就只能在火车站的寒风中,一面想念我的家人,一面想念我的大衣,就这样坐待黎明。
天色欲晓,同一车厢赴德的六个中国人,就唱起了“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举杯论英雄,光荣属于谁”这首歌,在年轻而欢快的歌声中,我们终于各奔东西。
初到联邦德国的奥根斯堡大学学习,出乎我的意料,给我触动最大的不是当时西德经济的繁荣,而是德国人无处不在的环保意识。
为了环保的缘故,学校里很多教授都放弃开车,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这在当时的我看来非常不可思议: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人,还觉得拥有一台自己的汽车是很了不起的梦想呢。
另一点触动我的事情,就是垃圾分类,不要说当时的国内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在北京这么发达的城市,同样也很难真正实施。初到德国,如何进行垃圾分类这件小事曾让我头疼不已,而对于德国长大的孩子而言,他们从小就受到垃圾分类的教育,对这些事早已习惯成自然。
还有就是那时候的德国超市,早就开始使用更环保的纸袋和布兜来装各种商品,反观国内,塑料袋却刚刚开始流行,渐渐成了购物时的必需品。
在德国,我继续自己的生意尝试。这些对环保的感受,一开始还没有让我有那种切身的痛感,直到我做了一笔巨亏的买卖。
那时我一到周末,就会去慕尼黑大学旁的二手车市场倒车,还真赚了一些钱。渐渐地,我做二手车生意是越来越顺手,我也痴迷于这种赚钱的感觉。
后来有一次,我看上了一台成色很不错的宝马525,以700多马克的价格买入。按照往常的经验,我觉得净赚300马克应该不在话下。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始料不及:这台宝马车居然是一个“大油桶”!年检时不符合德国当时的国家环保标准,如果我要转手,就必须至少花3500马克进行一番大修!我听了郁闷之极,左想右想,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一个避免损失的方法,最终只好认栽,以1马克的价格把它卖给了旧车场。
就是这么一笔买卖,让我以几乎赔光的结局真真切切地上了一堂环保课,让我意识到在德国环保的重要性,也启蒙了我在考虑商业问题时的环保意识。
当时我去德国留学,属于自费公派,拿的不是中国政府的钱,而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奖学金,所以经济压力也并不算大。可是天性就不安份的我,总是时时处处都在琢磨有什么赚钱的机会。
去了德国还不到半年,我就用自己赚到的钱开始尝试买股票,那时候我全部的积蓄有3万马克,全被我投进去买了大众汽车。买入后仅仅两周,1987年的黑色星期五股灾,就犹如暴风骤雨般爆发,我买入时400多马克一股的大众汽车,一下子就被打到了190!当时我就慌了神,赶快去向一位师兄去讨教。我问他,这个股票会不会把我的钱都跌没?这个师兄也根本不懂,他说:“你的股票确实可能最后会一分钱都不值!”吓得我赶紧割肉,在略回升的200马克左右斩了仓。谁知道,又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大众汽车涨回了300多马克,后来又一直上涨,涨到了2000马克……这就是资本市场给我的第一次下马威。
在留学期间,我做过各种小生意,折腾过各种投资,这些经历就是我最大的财富,帮助我开拓了视野,也一点点地磨练了我在商业上的基本感觉。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思想意识上,这段经历都给我以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最扎实的基础。
把水溶性漆产品引入到中国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祖国。从1994年开始,我做起中德进出口贸易。最开始,只是将中国的丝绸领带等产品出口到德国,可是这样简单的进出口贸易,终究不能让我满足,初步的试水之后,我开始考虑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
我想起自己早年在德国所感受到的环保事业对我的震撼,那好像是埋藏了多年的一颗种子,现在就要生根发芽了。我开始认真思考,是否能够把德国好的环保产品带回中国,为改变国内的环保现状出一份力。
正是在这个期间,我从小就认识的一位邻居大叔,他一直在做油漆工,由于常年跟味道刺鼻的油漆打交道,患上了职业病,五十多岁就倒在自己的岗位上。听到这个消息,让我萌生了回国去经营环保涂料的这个更具体的想法。
经过亲身考察,我发现国内大量使用的都是在欧洲已列入淘汰名单的有毒、致癌的溶剂型油漆,因此每年得病的人越来越多。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光是因有毒有害装修材料而罹患白血病的儿童就超过200万!这是多么可怕的现状!
于是我下定了决心,要把在德国普遍使用的水性漆产品引入中国市场——水性漆是一种以清水作为唯一稀释剂,不含有苯、二甲苯等有机溶剂、不需固化剂的漆产品。它无毒无味,涂刷后即可入住,在欧美的普及率当时就已经很高了。
1996年,在德国科隆召开的两年一度的涂料展会上,我一连几天都泡在会场里,就是为了反复地比较各个大型环保涂料生产商的产品。最终,我选中了欧洲最好的水性漆品牌——德国都芳漆。
我直截了当地跑去告诉拥有这个品牌的德国梅菲特工业集团的董事长,说我要做他们在中国地区的总经销,他们既不用负担我的房租,也不用负责为我投广告,只是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在一段时间之内不要把赚钱放在首位。”我对他说,“这样我就能打开中国的市场。而且,我要在中国独立注册商标。
当时,我几乎花掉了自己所有的现金,购买了两个40英尺货柜的水性漆发往中国,这让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大感意外,同时也感受到了我的决心和诚意。
最终,我采取买断产品取得亚洲总经销权的方式,成为了德国都芳漆亚洲区唯一总经销商。这样,我就成了第一个将高品质水性漆产品引入中国的人,从此结束了中国没有水性漆的历史,都芳漆在中国也几乎成了环保漆的代名词。有些媒体开始称呼我为“中国环保漆之父”,“中国水性漆第一人”等,而所有这些,其实还是离不开留学经历带给我的环保和商业方面的启蒙。
用感恩的心情再续儿时梦想
现在,说起喻恒,一般都是带着两个title,除了“中国水性漆第一人”,另一个就是“海归收藏家”。
不错,随着事业进入稳步发展阶段,我得以从繁琐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抽身,发展一下自己的书画收藏爱好。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甚至重拾儿时的梦想,也是我父母最早在我身上寄托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小提琴。
我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出生和长大。我的祖父就是一位牧师,并曾经长期担任中国基督教会主席,我的父母也都是从小在教会学校里长大。教会的传统,是有很多西洋音乐的熏染,所以我热爱音乐的父母从小就培养我拉小提琴,并且希望我长大后能够登台去表演。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远赴德国的时候,除了基本的行李,还要带上我那把小提琴的缘故。在留德期间,周末的宿舍里,一旦有联欢活动,我出的节目总是拿出小提琴为大家演奏一曲。
进入收藏领域以来,最近小提琴也成了我的一个重要的收藏方向。尤其是去年拍下了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杜庞将军”以后,我又重新回到了儿时每天练琴的时光。通过一年专注、勤奋的练习,我也最终实现了登台演出的多年夙愿。
最近一年来,我不但和吕思清在保利大剧院合作过二重奏,还在德国柏林音乐学院登台进行过小提琴独奏演出……
我感到庆幸,我的很多梦想都能够实现。这时候,我又会有下一步的目标。我会用我所有的能力去带着感恩的心情,回馈这个世界。在我看来,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感恩的回报。
走笔至此,我内心里酝酿的一个决定也水到渠成:我决定将“杜庞将军”借给齐默尔曼三年,以帮助当今世界公认的最顶尖小提琴家之一渡过暂时的难关。
也许如同我们自身一样,“杜庞将军”也只是这个大千世界中的一位游子,只有到了知音者手中,它才如同游子归家,才会焕发出真正属于它的无穷魅力和神采。而齐默尔曼也向我做出承诺:一定要为中国的小提琴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定期来中国举办大师班,提携中国的年轻小提琴家。他也将于2016年的1月份,在柏林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球媒体公布他获得新欢——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杜庞将军”——的消息。
同时,我也将开始着手筹备成立自己的“喻艺术基金会”,目标是将收藏的名琴赞助给一批中国青年小提琴家使用,提供奖学金给优秀的学生和赞助音乐活动及相关比赛。
回首这一切,留学生涯确实是改变我个人世界的关键,这段经历打开了我之后的整个人生。现在又写下这篇文章,在行文即将结束的时候,往事的点点滴滴却又不断地浮现在我眼前:
那些严谨专业的课程知识,那些值得学习的德式习惯,那时和中国留学生一起做的家乡菜,那时常在宿舍里拉起的小提琴……
时光的雕刻,让这些美好往昔都成了如诗般的回忆,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上,我将把它们一直都珍藏在心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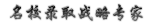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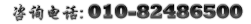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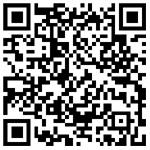








 香港SAT“万人
香港SAT“万人
 世界著名大学:“
世界著名大学:“
 世界著名大学:精
世界著名大学:精
 世界著名大学:魅
世界著名大学:魅
 发现了飞越大洋的
发现了飞越大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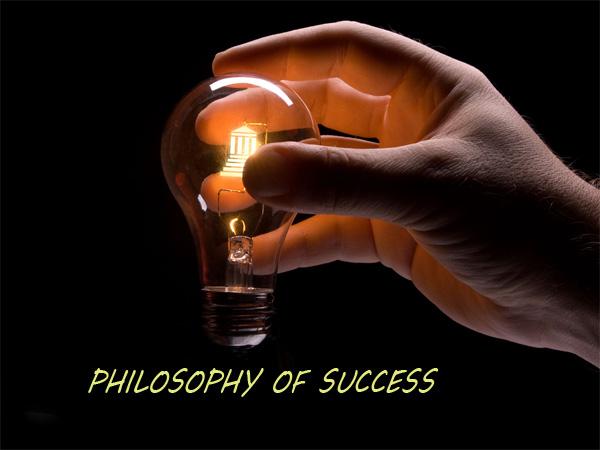 温和的成功哲学
温和的成功哲学
 本杰明·瓦伦斯:
本杰明·瓦伦斯:
 学校扼杀创造力
学校扼杀创造力
 可汗学院公开课:
可汗学院公开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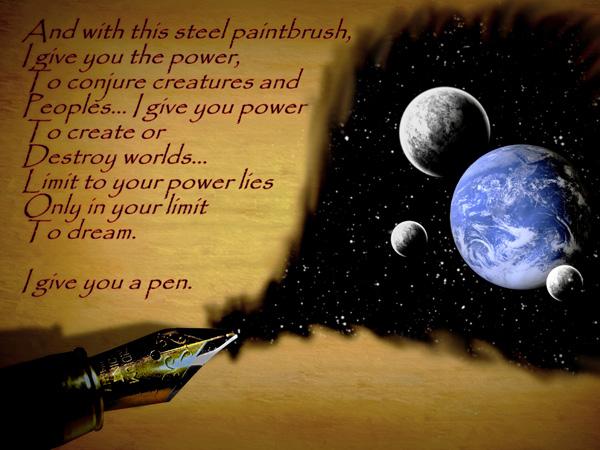 耶鲁大学公开课:
耶鲁大学公开课:
 纽约大学公开课:
纽约大学公开课:
 哈佛:新媒体时代
哈佛:新媒体时代